唐宋文化论坛的范文 第一篇
唐王朝在对以前历代设置经验的基础上,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置上实行羁縻都督府、羁縻州、羁縻县制度.这些羁縻府州的特点就是:规模小,变化大.唐朝对于羁縻府,州的设置,基本是把边疆少数民族置于唐王朝的统治之下.羁縻府州、县制度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少数民族传统的行政管理制度保留下来了而且把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国家统一行政设置之中,授予各族首领为唐朝地方政府,羁縻州都督,刺史等官,但这些官职都必须由 政府任命,同时,大部分民族地区取消了上层分子的可汗称号,这是为了 政府统治和行政管理的统一,从而避免了各少数民族的独立.唐王朝在对羁縻府州的管理上:在重要的地区设立都护府,如单于,安西、安化、北庭、安东、安南都护府;在其他地区设置都督府,以此督促那个地区的各民族羁縻府州.这样的设置加强了 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领导,确保了国家的统一局面,保证了各民族间的联系.
唐宋文化论坛的范文 第二篇
[摘要]茅坤在文学思想的建设进程中,曾与派内的唐顺之、蔡汝楠和派外的徐中行等人发生争论。正是在争论中,茅坤不仅摆脱了前七子派的古文宗法,而且成功超越了以唐宋文代替或包容秦汉文的思维局限,以地理喻文,提出神理说,建立了古文正统论。在将诗歌正统让与七子派的同时,茅坤又代表唐宋派坚决捍卫其古文正统地位。
[关键词]唐宋文派;七子派;古文正统;诗歌正统;文派争论
对明代唐宋派的文学思想,21世纪前的研究重点大抵是放在对其成员主要是唐顺之和茅坤的文学主张进行论点抽绎和定性评价上,进入新世纪,则似有了两个研究路向:一,以前一时期提出的相关命题为话域,以更细致的材料梳理为基础,以更准确的流派关系认识为理据,进行新的哲学思想、文化艺术精神的辨析、阐释和理解;二,对前一时期习以为常、几乎不加讨论的成员构成及称名缘由,进行新的梳理、厘定和阐说。对第二点,笔者以为,唐宋派是一个活动于前后七子派之间,且大部分文学主张与之针锋相对,在客观事实上存在的文学流派,只是其成员当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人为代表,归有光则不能算。对第一点,笔者以为尚须阐明这样两条认识:一,三人的文学思想各有相当复杂之发展历程,由于交往出现了共同性,这解释了他们共为一个文派的事实;二,三人的古文主张是在应对前七子派的余脉和后七子派的批判以及本派成员的不断争论中得以发展完善。正是批判与争论的存在,唐宋派才完善了其文学思想(主要是古文理论)的建设。
以上述思考为出发点,本文以茅坤的书信为中心,探讨唐宋派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派内派外之争,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学思想建设和现实的文派要求。派内主要是与唐顺之、蔡汝楠的争论,派外主要是与后七子派徐中行的通信;前者关乎文学思想的建设,后者关乎作为文派的文坛现实要求。
一、唐宋派的文学思想建设
以王、唐、茅为代表的唐宋派,其文学(主要是古文)思想建设大致都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按王、唐、茅的顺序,三人先后从前七子派的摒弃唐宋、高扬秦汉的古文宗法,转移到包容秦汉而分外重视唐宋(主要是以欧阳修、曾巩为代表的宋)的古文宗法;二,再由以唐宋文为宗进到泯灭秦汉、唐宋文界限的超越阶段,建立独立的主体精神,阐述严密的文章格法。之后,三人的古文思想各有不同呈现:王氏基本没再发展,,茅坤则继续建立其古文正统论,唐顺之则转向了性命和事功之学。
茅坤古文思想体系的建构主要是在派内与唐顺之、蔡汝楠等人的交流争论中得以孕育成型的。同王、唐一样,其古文主张最初也蛰伏在前七子派的古文宗法里,学习秦汉词句,模仿秦汉风格。其《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云:“仆少喜为文,每谓当跌宕激射似司马子长,字而比之,句而亿之,苟一字一句不中其累黍之度,即惨侧悲傻也。唐以后若薄不足为者。”到嘉靖二十二年(1543)与唐顺之相交后,受其影响,脱离了前此的字句模拟方式,转而习尚唐宋古文,但对唐顺之当时古文思想中的以唐宋文包容秦汉文的策略并不满意。其《复唐荆川司谏书》云:尝闻先生谓唐之韩愈,即汉之马迁;宋之欧、曾,即唐之韩愈……古来文章家,气轴所结,各自不同。譬如堪舆家所指“龙法”,均之萦折起伏,左回右顾,前拱后绕,不致冲射尖斜,斯合“龙法”。然其来龙之祖,及其小大力量,当自有别。窃谓马迁譬之秦中也,韩愈譬之剑阁也,而欧、曾譬之金陵、吴会也。中间神授,迥自不同,有如古人所称百二十二之异。而至于六经,则昆仑也,所谓祖龙是已。故愚窃谓今之有志于为文者,当本之六经,以求其祖龙。而至于马迁,则龙之出游,所谓太行、华阴而之秦中者也。故其为气尚雄厚,气规制尚自宏远。若遽因欧、曾以为眼界,是犹入金陵而览吴会,得其江山逶迤之丽、浅风乐土之便,不复思履毅、函以窥秦中者已。大抵先生诸作,其旨不悖于六经;而其风调,则或不免限于江南之形胜者。故某不肖,妄自引断:为文不必马迁,不必韩愈,亦不必欧、曾;得其神理而随吾所之,譬提兵亦捣中原,惟在乎形声相应,缓急相接,得古人操符致用之略耳。而至于伏险出奇,各自为用,何必其尽同哉!
他以为唐顺之的策略矫枉过正,说明:第一,唐顺之尚未超越秦汉、唐宋文界限,是一种以唐之韩愈、宋之欧阳修、曾巩代替包容秦汉之司马迁的方式,可说只是为钝根人开的方便法门,带有临时的应付性质。因为它未能阐明秦汉文和唐宋文在古文学习中的复杂关系,毕竟秦汉文不能简单地就被替代或包容,其间仍存在价值和风格的界划。当然,这也是唐顺之(包括王慎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思想阶段,他们首先得让大众从前七子派秦汉宗法的沉疴里挣脱出来,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与前七子派不同的古文写作宗尚主张:前七子派“唐以后若薄不足为”,他们则要提倡“唐以后”文。宗法问题的现实针对性和迫切性使得他们的古文策略露出了设计的破绽,而这些破绽还得靠他们思想的继续前行来完善超越。在唐、茅相争时,唐也还未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于是给刚挣脱前七子派古文宗法的茅坤以辩驳的口实。
第二,茅坤抓住了唐顺之策略中的模糊之处,而代以明确的观“龙法”。他把古文按时序划为四大块,并赋予相应的堪舆分配和价值层级在其设计中,六经、秦汉、唐宋文的价值层级和堪舆分配是固定的,决不能随便挪动。用简单的算术表示,就是:六经>秦汉>唐>宋,司马迁>韩愈>欧曾,昆仑>秦中>剑阁>金陵、吴会。因此,在茅坤看来,唐的“包容”策略,至少犯了两个错误:随便挪动位置;以小包大。以此为基点,他倡导的学习顺序是由宋至唐至秦汉至六经的上溯,决不能如唐顺之目前的止于小之唐宋。此设计堪称精巧,但亦不免呆滞,于是又补充提出“神理”说,算是从前七子派脱出的成果。有此认识,他就既不满前七子派的文必马迁说,也不满王、唐的文必唐宋说,如此也算超越了秦汉唐宋之限。
大体说来,茅坤的观“龙法”流于死板,近似于七子派的格调,而其“神理”说趋向虚灵,近似于王、唐的独立精神,然两者的混杂,也说明茅坤未能真正超越秦汉、唐宋之限,于是遭到了唐《答茅鹿门知县一》的反驳:来书论文一段甚善。虽然,秦中、剑阁、金陵、吴会之论,仆犹有疑于吾兄之尚以眉发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也。若以眉发相,则谓剑阁之不如秦中,而金陵、吴会之不如剑阁可也。若以精神相,则宇宙问灵秀清淑瑰杰之气,固有秦中所不能尽而发之剑阁,剑阁所不能尽而发之金陵、吴会,金陵、吴会亦不能尽而发之遐陋僻绝之乡,至于举天下之形胜亦不能尽而卒归之于造化者有之矣。故日:有肉眼,有法眼,有道眼。语山川者于秦中、剑阁、金陵、吴会,苟未尝探奇穷险,一一历过而得其逶迤曲折之详,则犹未有得于肉眼也,而况于法眼、
道眼者乎?愿兄且试从金陵、吴会一一而涉历之,当有无限好处耳。虽然,惧兄且以我吴人而吴语也。
此处唐氏即攻击茅坤观“龙法”说的拘泥。事实也如此,茅坤尚未完全摆脱前七子的思维模式,仍要在秦汉文和唐宋文问强作价值的高下区分,就不免受到唐的善意嘲弄:只是“以眉发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仍是以“肉眼”而不是以“法眼”、“道眼”观物;如以“精神”、“法眼”、“道言”观文,则秦汉、唐宋各有其至,不得强分高下,更不得以“风调”来论定。斯言虽轻,却攻击了茅坤的喻证漏洞,戳穿了其观“龙法”与“神理”说的脆弱联系。不过,茅坤以地理言文的观“龙法”,却为其后来的古文正统论打下了思维基石,其“神理”说也发展成了《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的“文必求万物之情而务得其至”理论。
该书内容庞杂,归纳有如下数端:第一,从自己宦场遭贬黜的经历出发,提出要学习司马迁“发愤著书”的精神,一意以著书作文为业,以求名传后世,稍寄其悲愤之情;第二,在“圣学”和“达巷”之间,他选择了近于文学创作的“达巷”,提出“盖万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人以聪明智慧操且习于其间,亦各有所近,必专一以致其至,而后得以偏有所擅,而成其名”的观点;第三,回顾为文历程,说自己走出了前七子派的古文宗法,摆脱了字比句拟的模仿习惯,在和唐顺之的交流中,加深了对上述观点的认识,并以其读司马迁传记的心得,明白司马迁的伟大乃在于其能“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并称这个心得乃是“此庖牺氏画卦以来相传之秘”。
蔡氏《答茅鹿门》驳议的中心就是茅坤的立言不朽,要他归宿于圣学的“考德”。第一,批评茅氏树为典型的司马迁、韩愈等人,认为他们“遂多太过不安之词,非有德雍容之象”,以“通于论道”的名义攻击茅氏藉以发扬的不平则鸣说;第二,集中批评司马迁的“不自知”和不懂立言的“直婉”原则,阐明“故立言者,夫子之末节,而夫子汲汲于修德为先,忠信为业,为吾人安身立命之学。”第三,强调修德省心为本,立言作文为末,希望茅氏进于圣贤“至德”的心性之学。由此可见转而趋道的文章之士在选择安身立命的归宿时,却往往断绝了立言不朽的途径。
但茅坤并未放弃为文的念头,而是吸收了蔡氏的六经为准之论和“道”,走进了文章正统论的建设。观《复陈五岳廷尉书》《复陈五岳方伯书》可知其仍津津于这次“天地万物之情、各有其至”的议论,以为循此,“学者惟本之吾心,以求之六藉之深,则固有释氏所谓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者。”颇以为得千古文章之秘。这个议论引来了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二》的好评,以为与己见大同小异。
由上可见:第一,《与蔡书》是茅坤的古文理论超越秦汉唐宋之界的标志;第二,唐宋派的文论决非如人们所言的一直就只提倡唐宋文,而是在不断发展,有一个由包容秦汉到超越秦汉的过程;第三,论争对文学思想的建设有重要作用,正是在通信交流中,一些主张才得以明确,理论才得以完善。
抛弃了《复唐荆川司谏书》中观“龙法”的呆滞,留下其以地理喻文的合理因素,再渗入由“神理”说发展而来的“万物之情、各得其至”理论,茅坤的古文正统论已经呼之欲出了。有多条材料表明,这个理论在嘉靖三十三年就已经成形,并由万历七年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及其《论例》公诸于众,流传四海。有关的书信文献还有《文旨赠许海岳沈虹台二内翰先生》、《与沈虹台太史书》、《与徐天目宪使论文书》、《与王敬所少司寇书》、《复陈五岳方伯书》等。可见其正统论也仍然是在与他人的交流中完成的。
二、唐宋派的文派要求
所谓文派要求,即是一种文学思想、主张,也即话语权在古文写作层面的要求、展开和实现。对唐宋派来说,其文派要求主要集中在古文领域,对诗歌领域他们要么归宿在七子派的诗歌宗法里如王慎中,要么先有所展拓而后归宿于已形成传统的性气诗最后又放弃了文学兴趣如唐顺之(包括晚年的王慎中),要么自行逊让如茅坤,总之要求不多,现实效果也不显著,这也是我们将唐宋派定性为文派的根本依据。
唐宋文化论坛的范文 第三篇
摘要:韩愈散文接受是中国古代散文接受史的重要架构,是建构中国古代散文史的关键环节。一部由元至清的韩愈散文接受史就是一部中国古典散文成长史,研究好韩愈散文技法和理论的接受脉络有助于勾勒中国古代散文接受史的基本框架,对最终形成一部系统完整的中国古代散文接受史的意义不言而喻,这也是本文的目的。
关键词:元明清;韩愈古文;接受状况
韩愈中国文学史上最出色的散文家之一,以丰富而卓越的散文创作成果,占领了被骈文统治多年的阵地,宣告了古文对骈文斗争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比如茅坤把他和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杜牧把韩文和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为“文起八代之衰”,但都语焉不详,不能详细了解韩愈在散文史中的地位和贡献。以下力图对韩愈古文在元明清这一历史时期的接受状况做一个简要的论述。
(一)韩愈散文在元代
元代文学创作成就不比唐宋,文学领域戏曲独胜,诗文等传统文学样式一向凋萎。因元朝理学盛行,以弘扬道学为旨归的韩愈散文继续受到关注。总体上,元代前期文坛受科举的制约,言理道性成了文学的共同使命,对韩愈、欧阳修等唐宋名家名作的模拟成了一时之气;延v以后,科举废弛,文学创作松绑,文坛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但还是存在崇拜、学习韩愈散文的文学名士,比如袁桷。元代文坛虽宗欧阳修、苏轼,但对韩愈散文也是很重视的,因为元代文人知道欧、苏文章的根脉在韩愈那里。元代前期文坛有郝经、姚输、姚燧、戴表元等人对韩愈散文有过较为深入的研究。金元时人对韩愈散文的研习除了与唐宋文人一样,肯定韩愈的文学史地位和鉴赏韩愈散文的美学特征外,尤其注重对韩文文法的研究。韩愈散文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四方面:其一,论心法。心法是金元士人鉴赏接受韩愈散文所关注的最高法则,郝经称之为“大法”。主张文章的最高法则就是要明白“理”与“法”的关系,“精穷天下之理”并指出儒家经典是“理、文、法”兼备的最高、最好的学习蓝本。这与韩愈文论有相通之处。其二,论“篇法”。其三,论“句法”。古人作文都很注重句法,唐宋皆然,郝经说:文章“至韩柳欧苏氏”已“句句有法”。其四,论“字法”。金元文人论文很重视“字法”,郝经又说“至韩柳欧苏氏”已“字字有法”。元代文人接受韩愈散文特别注重对韩愈散文的评点批注,王若虚的《滹南遗老文集》和程端礼的《昌黎文式》是代表性的作品。相比较而言,程端礼的《昌黎文式》注重对韩愈散文的点评,从字法、句法、篇法和艺术风格等方面进行批评,这种方法对当时学者学习韩愈散文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实用性很强,便于学习模仿[1]。
元代散文有“文擅韩欧”的基本特点。前期姚燧,元明善等崇唐,偏重奇崛雄健,尚韩愈;刘因、王浑等崇宋,偏于平易温醇。后期二者界限不太明显,逐渐趋向唐宋并崇[2]。在文道关系上,元代散文有重道轻文的倾向,因而元文大多偏向实用和明道,在性情的抒发和文词的华美方面有所欠缺。元代诸家往往在宗韩和宗欧之间有所取舍。元代文坛自延v年间才开始学习韩愈的文风向欧阳修的文风回归。谢枋得所编《文章轨范》所选文章最多的是韩愈,有32篇,苏轼12篇,欧阳修仅5篇,并非谢枋得对此有所偏见,而是要为科考举子提供考试模板,韩愈、苏轼是最佳模仿对象。这些都显示出韩愈对元代散文的贡献。
(二)韩愈散文在明代
(三)韩愈散文在清代
清代的散文,具有终结性和过渡性的特点,散文名家不多。黄宗羲为文,强调“情至”与文、道、学的统一,清初的汪琬为文受唐宋派影响,以八大家为法式,都有过潜心研究和学习韩愈的散文的经历。清代散文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由方苞始创于康熙朝,一直绵延至清末。该派文学主张近宗明代的唐宋派,远接唐宋八大家,以“义法”为中心,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前人的基础上作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6]。“义法”说使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关系更加密切,文章写作要“有助政教”,这一观点也是对韩愈的“文”与“道”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乾隆、嘉庆时期,属于“桐城派”或写作倾向相接近的散文作家,主要的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刘开、姚莹、朱仕诱等人。管、方、刘、姚诸人重气势,比如,方东树说:“韩公当知其“如潮”处,非但义理层见叠出,其笔势涌出,读之拦不住,望之不可极,测之来去无端涯,不可穷,不可竭。当思其肠胃绕万象,精神驱五岳,奇崛战斗鬼神,而又无不文从字顺,各识其职,所谓“妥贴力排S”也。韩公诗,文体多,而造境造言,精神兀傲,气韵沈酣,笔势弛骤,波澜老成,意象旷达,句字奇警,独步千古,与元气侔。韩公笔力强,造语奇,取境阔,蓄势远,用法变化而深严,横跨古今,奄有百家,但间有长语漫势,伤多成习气。”(《昭昧詹言》)朱仕诱以荀况、司马迁、韩愈为师,尤其以学韩愈自命,“其文体格极正,宁艰涩而不肯不工,宁晦滞而不肯不奥,专于炼句炼字,雕琢太过,往往意为辞累”,“晚年文从字顺,渐近自然,神到之篇亦自入妙”,比较追求阳刚之美,与方苞、姚鼐风格稍异[7]。
可以看出,韩愈散文影响在清代仍然很大,但已经减弱。
唐宋文化论坛的范文 第四篇
我觉得还是客观因2113素决定的。5261唐朝的建立是经过几百年的战乱后,人口数4102量急剧减少,土地1653大量荒芜。而且再加上当时的民族成分复杂,这样这个思想较为没有束缚,所以多种思想可以百家争鸣,国家的环境较为好。所以当时社会的思想还是比较开放,文化较为有活力。对于变革也看得很开。而宋朝,人口已经很多了,而且儒家思想已经基本确立,民族较为单一。随着人口的增加,思想的单一,宋朝的文化也日趋保守。人口的增加,使得国家必须将重点放在统治人民,保证人民正常的生活,对于变革则始终是否定的态度,因为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口,任何小变革都不是小事情。所以才有了儒家思想的标榜,儒家思想反而在影响民族文化,于是就产生宋朝的文化,从而影响中国1000年。
唐宋文化论坛的范文 第五篇
一、古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一)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庄子》、《楚辞》、《史记》和陶渊明等的接受研究。杨柳《汉晋文学中的〈庄子〉接受》(巴蜀书社2007年版)从庄子生命意识、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说方式三个方面来探讨汉晋文学对庄子的接受,著者认为《庄子》强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汉晋士人和文学对其进行选择接受的一个主要兴奋点。白宪娟《明代〈庄子〉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从文学、注本和理性阐释三个方面来探讨明代《庄子》接受的纵向走向。《楚辞》的接受研究虽然还没有专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论述文章。如刘梦初《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2002)、《论李商隐对楚辞的接受》(2002)、《试论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契机与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2005)、蒋方《唐代屈骚接受史简论》(2005)、张宗福《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2008)、叶志衡《宋人对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这些文章主要是探讨唐人对屈原《楚辞》的接受情况。
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和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别对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记》接受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渊明接受分为三个时期,即奠基期(东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和高潮期(两宋),并且力求从共时形态和历时形态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陶渊明接受史的探讨。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诗的发展线索,全面而有重点地描述了唐人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接受的历史特点,阐述了陶诗与唐诗之间复杂的、深层的关系。田晋芳《中外现代陶渊明接受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则探讨了现代的陶渊明接受情况,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接受,视角较独特。此外,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汉代—隋代)》(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罗春兰《鲍照诗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王芳《清前谢灵运诗歌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分别对汉乐府、鲍照诗歌、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唐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接受研究。台湾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的著作,对李白诗歌接受进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来,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则对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较为具体详细的论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个阶段加以探讨。台湾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对杜诗的唐宋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黄桂凤《唐代杜诗接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则专注于唐代杜诗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诗接受分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个时期。杜晓勤《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1991)、《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1995)等论文则专门论述了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系统地探讨了韩愈诗歌在宋元的接受情况,认为“以文为诗”是韩诗与宋、元诗人在艺术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线索。
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从韩愈的儒学思想、文学思想、诗歌与散文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宋人对韩愈的接受情况,指出宋代对韩愈文学的接受是在北宋时期,到南宋则渐趋衰弱。刘磊《韩孟诗派传播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韩愈、孟郊等人的诗歌传播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杨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学接受史》(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探讨了唐宋时期柳宗元的接受情况,特别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为详细,先是总论,后是分古文和诗歌两方面来论述。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分为“历代接受概况”、“阐释史”、“影响史”三个部分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史,重点是“历代接受概况”,以大量的文献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来的接受历程。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认为李商隐诗歌在理学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隐诗歌接受的重要时期。全书从虞山派、娄东诗派、黄任和康雍诗坛、黄仲则及乾嘉诗坛、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吴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顺鼎、清代女诗人等地域文学、家族文学和女性文学几方面来探讨清代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
李丹《元白诗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四人的诗歌在唐五代和两宋时期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此外,尚永亮《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2009)、赵艳喜《论北宋晁迥对白居易的接受》(2008)等论文对白居易的宋代接受进行了论述。陈文忠《〈长恨歌〉接受史研究》(1998)、陈友康《〈长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2000)等论文则对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此外,白爱平《姚贾接受史》(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对贾岛、姚合并称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研究;张朝丽《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2004)、陈友冰《李贺诗歌的唐宋接受》(2008)等论文对李贺诗歌接受进行了探讨;李春桃的博士论文《〈二十四诗品〉接受史》(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接受进行了论述。五代时期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以《花间集》为典型。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花间集》的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范松义《宋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10)、范松义、刘扬忠《明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04)等论文也对《花间集》接受进行了研究。
(三)宋金元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宋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人的接受研究。张璟《苏词接受史研究》(_出版社2009年版)注重于“变”的立论点,从文体正变、词史流变、词风消长、时运盛衰、才性各异等各个方面,对苏词在宋金元明清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仲冬梅《苏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对苏词接受情况也进行探讨。陈福升《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梳理和研究了柳、周二人之词在历代的接受情况。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讨了辛词的接受情况,上编从南宋庆元以前到当代各大学通行的词选本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18种选本作为抽样调查的对象,以总结归纳历代辛词接受与消费的规律;下编通过自南宋至近代王国维的评论,探讨批评史中的辛词接受情况。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则对清代辛弃疾词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时期稼轩词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宋元时期辛弃疾词接受进行了探讨。陈伟文《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清代前中期的黄庭坚接受情况进行较为详细地的研究。金元时期的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以元好问和《西厢记》接受研究为代表。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把元好问诗歌接受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形成时期(金元)、曲折发展时期(明代)、高潮时期(清代)。全书主要是梳理各个时期诗评家对元好问诗歌的阐释、诗人创作受到元好问诗歌影响的情况,并辅以选本、集本的效果和传播研究。伏涤修《〈西厢记〉接受史研究》(黄山书社2008年版)从刊刻、选本与曲谱收录、演唱、本文批评、题评考订、改续之作、文学影响等各方面探讨了《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
(四)小说接受个案研究
古代小说的接受研究成果很少,最早以接受来研究小说的专著是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1992),但该书更多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探讨。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水浒传》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把《水浒传》接受史分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现代和当代几个时期。郭冰《明清时期“水浒”接受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则对明清时期的“水浒”接受进行了探讨,分统治者、文人和民众三个层面来论述。宋华伟的博士论文《接受视野中的〈聊斋志异〉》(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对《聊斋志异》的接受进行了论述,分古典接受阶段、建国前的现代接受、建国初期的接受阶段、新时期的接受阶段几个时期,并考察了《聊斋志异》的域外接受情况。
二、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反思
无庸置疑,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借鉴外来的接受美学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方面,经过磨合、融通和拓新后,广泛地运用到古代文学研究当中,不仅使外来理论得到了本土化转换和运用,而且开拓了从读者接受视角研究文学的新视野,促进了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古代文学接受研究十分注重经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这既充分体现了“经典”的艺术价值、艺术魅力和艺术影响力,也展示了研究者对于“经典”研究对象选择的学术锐敏性,有助于几千年的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得到当代重估和转化,有助于传统文化在当代复兴和繁荣。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古代文学接受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接受理论的进一步转化和深化问题
接受研究强调从读者视角来研究文学的传播问题,而读者接受往往是与文本传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何区分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现实难题。如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虽题为接受史,但一些章节内容涉及到传播的问题,如元好问诗文集编定、刊刻显然是属于传播范畴。而有些问题的讨论则很难区分是传播还是接受。像元好问诗歌的选录研究,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它是传播范畴;从诗歌选录者来看,它又是接受范畴。再如清代元好问诗歌的评点与笺注,从评点与笺注者来看,属于接受范畴;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又属于传播范畴。尽管有些学者已经对文学接受的理论作过一些探讨,并且有过文学接受研究的学术反思,但这些理论和反思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圆满解决研究中的难题。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理清接受与传播、接受与研究的本质区别,这样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开拓研究新境界。要真正解决传播与接受的区分,突出文学接受,还是应该抓住“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因为文学传播本质上是离不开读者接受的,没有读者接受就没有文学传播,在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下,既可以厘清传播与接受的区分,也可以对传播材料作接受解读,从而深入探讨文学接受之于传播的价值和意义。
二是接受研究实践进一步拓展和创新问题
古代文学接受研究以经典文学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宏观上的接受研究。其中,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庄子》、《楚辞》、《史记》、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无疑这些个案研究突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性,特别是唐诗和宋词的经典性。但无论是时代的分布上,还是研究对象的数量上,个案研究中经典作家作品都不具有广泛性,采集面显得较为狭窄。因此,突破唐诗宋词的视阈局限,进一步拓展经典作家作品对象采集是个案接受研究努力的方向。宏观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正如前面综述所论,其研究也在存较大问题。宏观研究一方面要从时间视阈出发进行通代或断代接受梳理,探讨中国文学的通代或断代接受情况;另一方面也要从空间视阈出发进行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情况,探讨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或被接受情况。同时,宏观研究还可从作家群体接受、作家流派接受、文学家族接受等方面来创新。宏观研究需注意主流文学与次流文学、主要作家与次要作家之间关系处理,否则宏观的接受研究就容易变成为个案研究的拼盘,而显示不出宏观接受研究所具高屋建瓴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三是接受研究的文化视阈问题
文学的接受选择离不开时代的文化背景、地域的社会风气和作家的主体思想等文化导向问题,因此接受研究不只是简单梳理一下某一作家作品的接受史或地域分布,同时还要关注其接受的文化本质倾向,要从文化哲学的理性高度审视文学接受的内在规律和外在原因,这样才能真正透彻地对文学接受进行深入研究。如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有些章节很注重文人接受《水浒传》的文化心态研究,如从遗民文化探讨了清初文人接受《水浒传》的时代情况。但这种文化哲学的探讨并未贯通全书,如对金圣叹的《水浒传》接受研究,尽管较为详细地分析了金氏的接受情况,却未揭示金氏“腰斩”《水浒》的文化成因和主观目的。任何文学接受都有其外在的文化背景和内在的主观目的,作为文学接受研究应该对此作深入挖掘,这样才能凸出读者接受的意义,而不仅仅关注于文本的传播。总而言之,古代文学接受研究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也存在一些现实困难和问题,相信经过学界的总结、反思和创新,会有新的突破和质的飞跃。
注:本文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立即后台留言通知我们,情况属实,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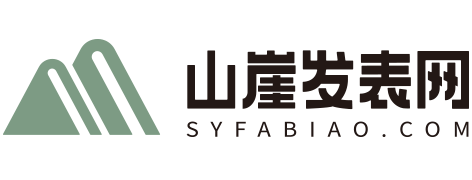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