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哥老会的起源 第1篇
关于啯噜在四川的出现,从乾隆早期官私便都有记载。个人对啯噜比较详细的观察和讨论,大概是邱仰文《论蜀啯噜状》和《再论啯噜状》。对于邱仰文,李调元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公讳仰文,号省斋,滋阳人,雍正癸丑进士,曾官南充知县。”雍正癸丑即雍正十一年(1733)。邱还著有《硕松堂集》,里面包括了上述两篇讨论啯噜的文章,都收在了贺长龄所辑《皇朝经世文编》的《兵政六·保甲下》。虽然不清楚这两篇文章写作的具体日期,但是根据邱中进士的时间,大概可以猜测他活动在雍正和乾隆前期,这给我们提供了那个时期啯噜的发展情况。
邱仰文的《论蜀啯噜状》称:“啯噜,良民之蠡贼也,婚姻之牍繁而廉耻丧,田界之讼积而任恤衰,此皆急宜清理者。而粮莠不除,嘉禾不生,非先治啯噜,则更化无由。”把治理啯噜作为当时诸种社会问题中最紧迫的事情,把婚姻、廉耻、田产官司等各种问题都放在后面了。啯噜是怎么兴起的呢?邱认为:“査啯噜种类最伙,大约始乎赌博,卒乎窃劫。”就是说他们开始于赌博,赌博就有输赢,输了就去抢劫。然后就有了各种犯罪活动,如“酗酒打降,勒索酒食,奸拐幼童,甚而杀人放火”。啯噜有两种,一是“红钱”,自称或互称“红钱弟兄”。那些由于犯法被“刺面”者,则“红钱不入”,而加入“黑钱”。
邱还说,啯噜之所以发展到如今的情状,“而害皆起于窝”,就是窝赌。“啯噜赌博,店家抽头是也”。但是也有“不得不窝者”,特别是那些“荒山孤店,畸零一二家,啯噜成群,力不能拒”。有的场镇由于地方偏僻,官府难以控制,结果造成啯噜聚集,“凶横盘踞,隐忍停留,莫敢究诘是也”;也有碍情面者,过去参加过啯噜,现在已经不在啯噜里面混了,而且已经有了家产,但是从前同伙来了,要聚赌,抹不开情面,所以给啯噜提供了方便。虽然“种类不一”,但是“均为地方害”。[3]
的确,清地方官拿获的啯噜成员随身都带有赌博工具。根据乾隆四十六年(1781)七月二十九日湖广总督舒常和湖北巡抚郑大进的奏折,七月二十一日,“营兵协同县役在该县五眼泉地方拿获啯匪彭家桂一名”。据他招供,他是四川奉节县人,卖酒为生,“本年三月初二日,在垫江小马溪地方始入啯伙”,共有四十一人,有头目二名,即陈升、罗恒,都来自四川忠州,其余伙党有黄大年、黄大富、王升、王连、汪连、匡贵、冯贵、陈因、刘中名、何大年十名,但是不知他们来自何处。此外尚有二十八人,皆不知其姓名。他们曾于三月十二日“随同抢劫过梁山马家堰场一处,又于四月初二日抢劫过高峰山场一处,复闻官兵捕捉,头人陈升、罗恒商议,欲往川北躲避,遂大家逃散”。当局从该犯行李内“搜出布衫、马褂、骰子、压宝钱文等赃物,当将人赃一并交宜都县收审”。[4]
后来邱仰文又写了《再论啯噜状》,按照邱的定义:“伏以啯噜者,匪类之总名也。”也就是说,只要是土匪,那么都属于“啯噜”。[5]据民国《宣汉县志》称,“初四川有啯匪,而无教匪。啯匪者,金川之役,官兵溃于木果□(原字不清),其逃卒之无归者,与失业夫役,无赖悍民,散匿川东北,剽掠为生。及官捕急,则以_为逋逃薮。又湖北襄阳败贼,陕楚籍居三之二,多窜入川,故一旦揭竿起战,斗如素习。”[6]这与邱仰文的说法不同,似乎是把啯噜的发展与大小金川之役联系在一起,是因为战后大量无业的兵卒和夫役没有生计,所以在川东、川北靠抢劫为生。当官方追捕的时候,便加入了_。
邱仰文认为,这些早期啯噜,其实都来自外省,不过“来自黔粤,十无一二”,主要是来自湖北,即“率楚省流寓为多”。其实他们在原籍的时候,“皆良民也”。清初四川“草昧人稀,移来即可占耕,俗名插业”。但是承平日久,百余年来,人口越来越密集,也没有多少土地可供开垦了,即“民居密比,几于土满”。结果大量人口来到四川,成为流民,即“流来如故,无业可栖,一经失所,同乡同类,相聚为匪,势所必至”。因为大量的人没有生计,就难免出现这样的团伙。[7]
关于四川啯噜,乾隆初便出现在地方大员的奏折中。如乾隆八年六月初六日,四川按察使姜顺龙奏请“饬严禁啯噜与聚众”,便说:“川省系五方杂处之地,外来之流棍颇多”,但是以“啯噜子”危害最大。报告称他们是“棍徒”,来自云南、贵州、陕西、湖北等省,“少则三五成群,多则数十余众,率皆年力精壮,亡命无赖”,从事抢夺、_、赌博、酗酒等活动,“小民被其害者,皆忍气吞声,莫敢与较”。姜顺龙说,啯噜子“均系不法流民”,如果他们“聚而不散”,就会成为“地方隐忧”。所以令各所属境内,“严行查察,驱逐出境,不许容留,致成党羽”。如果遇到有“生事扰民者”,则“加倍重处”,使他们“势孤而不敢逞凶”。[8]
乾隆八年十月四川巡抚纪山上奏,报告川省数年来有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外来“无业之人,学习拳棒,并能符水架刑”。他们还“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凶刀,肆行乡镇,号曰啯噜子。_劫掠,无所不为”。他们喜欢聚集在州县交界处所,“出没各有记认,羽党日多”。甚至胆敢与官府对抗,如果“捕役乡保或一禀报查拿,必致遭其惨毒,为害实甚”。官府到处张贴告示,答应“自首减罪”,以达到解散其党羽的目的。那些自首的人,都必须把“同类姓名”写出来,除了“记档存案”外,还方便以后“相机查拿究处”。纪山说,“此等啯噜,凶恶异常”,所以对首领必须严惩,一旦“拿获到案,即照光棍例治罪,或枷杖立毙,以其罪名揭示乡镇集场”。而其他胁从之人,则“照律饬审”。如果是“外来流棍”,就“递回原籍,永远不许出境”;如果是“本省奸民”,便责令乡保管束,定期“点名稽查”。[9]
乾隆九年十月初六日,山西监察御史柴潮生上奏,继续说着同样的问题:“四川一省,人稀地广,近年以来,四方流民多入川觅食,始则力田就佃,无异土居;后则累百盈千,浸成游手。其中有等黠强悍者,俨然为流民渠帅,土语号为啯噜,其下流民听其指使,凡为啯噜者,又各联声,势相应援。”称流民参加了啯噜,“强乞强买,凌压平民”。近些年来,他们“横暴愈甚”,有攫取财物者,有_妇女者,有杀人致死者,等等。奏折说:“啯噜皆有勇力技艺,党羽复众,地方官惟恃民壮捕役,可以指纵擒拿,而彼处人役至少,本已不敌,又偶一被获,其党即为报仇,以此人皆束手听其恣肆,乡村小民受其荼毒,莫可谁何?”[10]
总结哥老会的起源 第2篇
乾嘉时期的著名戏曲理论家、诗人李调元,也留下了一些关于啯噜的记载。乾隆末年,住在绵州(绵阳)的李调元,就啯噜的问题给绵州知州严作明先后写了三封信,即《与严署州论蜀啯噜第一书》《与严署州论蜀啯噜第二书》和《与严署州论蜀啯噜第三书》。李调元历任翰林编修、广东学政,因_永平知府,得罪了和珅,被流放新疆伊犁效力,流放途中被召还,发回原籍,削职为民,居家著述。李调元在《第一书》中,首先便引述了邱仰文所说“稂莠不除,嘉禾不生”,他十分同意邱仰文的看法,“诚哉是言也”。他还重复了邱对啯噜的描述(显然后面严如熤也采用了这个说法):啯噜和赌博有关,“盖啯噜种类甚多,大约始乎赌博,终于窃劫”。按照李在第一书中的说法,他们的恶行还包括:“酗酒打降,勒索酒食,奸拐幼童,杀人放火,或同伙自杀”,这些人称为“红钱”;还有“掏摸为生,掐包剪绺,犯法刺面”,称为“黑钱”。他们都带着武器,“皆带刀持棍,其短刀者曰线鸡尾,长者曰黄鳝尾,皆以形似而名,相争则鞘刀于棍,即为长矛,此啯噜情状也”。
李调元说这个团伙的危害,起源于窝赌,也基本上是邱仰文的原话:即“其害者皆起于窝”,窝赌者是为了利润,如啯噜赌博,“店家抽头是也”;也有“不敢不窝者”,因为在“荒山孤店,力不能拒”;要不就是在场镇,却“心力不齐”;或者就是啯噜势力太大,“若辈结队太多,凶横盘踞,隐忍留停者,是也”;还有“碍于情面”而窝者,如过去为啯噜,现在生活稳定了,并不再参与啯噜活动,但是如果从前的同伙来家,“牵引聚赌,既有挟制,复关颜面,不便却逐”;或者就是“因缘奸拐,若辈年幼者,名曰小兄弟,斗杀相争,皆由此起”。所有这些种类,“皆为地方害”。[14]
李调元提出了治理啯噜的具体办法,就是要以里甲为基础,首先要选对的人,也就是要“先清里甲”,其实就是地方社区的治理和控制。这样啯噜便“驻足无所”。那么谁来进行地方社区的治理呢?那就是“必先选保牌”,就是健全保甲制度。因为“川省五方糅杂,流寓无产者多”,那就要动员相应的人力来对付这些流民,请这些人员应该有相对的稳定性,所以“保正牌头,必选老干有田业、妻室者充之,谕令各户,门牌移去者缴除,新来者注册,此为第一要着”,也就是说,如果里甲组织得严密,就不会有啯噜之祸,啯噜就没有藏身的地方。但是必须要选好牌头和保正。许多人是无产者,到处流荡,没有恒产,甚至没有家室。如果这些人充当里甲的差役,就是有名无实。所以选择保甲人员,必须首先要有地产,必须有家室,还要认真登记。
第二是必须要认真管理,要确立“值日稽查”的办法。例如一个乡场,要弄清楚有几个保,每个保有几个牌,总计共有牌保多少,每日由哪个保、哪个牌值日,“付以印簿朱戳”,保甲牌轮流分查,“某甲保家,有无窝藏,登注明白,立时举发”。这样周而复始,不会增加纳税户负担,即“不累花户,但责保牌,月度一缴一换,则责任专而约束严矣”。
第三是必须“勤巡视”。巡视的方法,官员要亲自进行,如果派遣差役下乡,则“徒多差扰”,而且差役职小,也没有权威,所以“弹压为难”。李调元还给了几个例子:张捕厅至夏家湾,“为贼匪驱回”;周汛司至郭家沟,被“贼匪打轿”。因此,有实权的官员要“躬亲巡视”,特别是那些大的乡场、或离县远的地方、或在县的边界,“啯噜最易出没往来”之处,除“带役查巡”外,还要经常“减装轻骑,亲临其地”。
第四要明“赏罚”。如果发现有窝赌,就要“尽力根究”。如果发现任何保甲“徇隐”,一旦经过举报,便要“严责更置”。如果协助“拿获啯噜到官”,则官要“亲给红花以鼓励之”。还要断了“贼匪”的后路,“毁其坊巢”,谕令那些有可能成为啯噜藏身地点的人家“别寻生业”。鉴于啯噜经常“结队横行”,则应该在各县的场镇,每家每户准备大棍,上面要书“专打拒捕啯噜匪类”八个大字,“立于门首,以鸣锣为号,齐力擒解”。但是对于已经抓捕的啯噜,“不得攒殴”。
这四条基本上都是模仿上节提到的邱仰文的办法。李调元预言,如果上述各种措施得当,“啯噜必闻而远遁”,那些与啯噜有瓜葛的人,也会“自顾其身家而不为矣”。当然,要让乡民“皆有耻而无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非一朝一夕之故”。他还给知州严作明戴了一顶高帽子,说“明公自到任以来,日惕息于驱匪”,但是近来以江万明、江万志兄弟为首的“啯匪”,仍然横行于南村、河村“两坝”。为什么“匪卒不能驱”呢?所以亟需改变办法,方能有效。[15]
不久他又写了《第二书》,他说第一书提到的江万明、江万志“已经殴毙,阖州称快”,但是仍然“有株根未尽者”,那就是夏家聚、陈单枪,他们进入他李家的“醒园”,居然在白天抢劫衣物,他已命家丁擒获,送交官府。他自己被啯噜祸害的亲身经历,让他感觉到地方官吏和役卒的不作为。窝户是啯噜的“总头”,而捕役则是啯噜的“护身”。因此,“窝匪不去,则啯匪难除;而捕役不清,则啯噜难尽”。而窝与役其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李提出,“故清窝之法,尤必先清捕役”。总是里外有人,啯噜才可以为非作歹,也就是“远贼必有近脚,坐地亦可分赃”。他举例说廖老四“乃啯噜之头目也”,藏在里甲宋士义的家,而且已经“下甲百三十人呈报在案”,但是下甲的捕役王燮“又从而为之隐分肥”,既然有好处,所以根本对此事不加理睬,“所谓根株之未尽也”。其实,地方上人们都知道啯噜的“情状路径,藏匿寄顿”,更不要说捕役了,“知之为最悉”。但是为什么用捕役来治啯噜,“又百无一效”呢?因为啯噜其实与捕役有勾结,犯案后逃到另一个县,“各捕声息相通”,他们狼狈为奸,结果却是“终日捕盗,而盗不息”,因此只有“慎选差役”。
那么怎样“慎选”呢?其实就是李调元在第一书里已经提出过的,他现在重新强调:凡是当差役的人,必须是有田产、有妻室的人,而且还是“明白强干老练者”。这里的“差役”,就是指“捕役”(或者称“捕快”),也称为衙役,其职责就是缉捕犯案人员。而“快壮各班”,不加以“捕役”的名号,以本地居民充当。所谓“快壮各班”,就是指县衙门的三班中的“快班”和“壮班”(外加“皂班”,又叫“皂隶”,在衙门里做守卫)。快班又称为快手,负责日常传讯、巡逻等,因此要选择健壮的百姓做杂役。李调元建议,捕役要密切注意“某场、某店、多窝、或暂留、或久住”,对于这一切都要了解。捕役要“蹑其踪,而防其弊”,随时“指名查拿,一有疏脱,惟捕役是问”。其行动还必须快,就是“雷动风行,出其不意”。只有这样,才能使“里甲保牌,相济为功”。人不必多,但是效率要高。[16]
后来,李调元又写了第三书,主要讲了一个故事。说是他最近“偶阅邱粟海《柴村集》”,对里面的一个故事有感而发。邱粟海即邱志广,字粟海,顺治时期曾担任长清县的训导,也就是县里负责教育事务的小官。这个故事是讲“以鼠捕鼠”,说有人非常恼火家里多鼠,而家里的猫根本不抓鼠,便想了一个办法,取雄鼠若干饲养,等非常肥大而壮的时候,又关起来,不给它们喂食。“急则相食,兽之性也”,也就是说,饿急了,强壮的老鼠,一放出来就吃自己弱小的同类,“弱者皆肉之矣”。然后按照同样的办法,反复折腾,“强与肥相捕,而尤强者出”,也就是说,当弱一点的老鼠被吃完以后,强的老鼠被特强的老鼠吃掉,最后只剩下最强的那只老鼠。“此鼠何以独存”呢?是因为其“黠而健”,就是又聪明,又强壮,所以能“食鼠以自肥也”。由于“习与性成,亦自忘其为鼠矣”,就是说它已经失掉了“鼠性”,“其行鼠也,其性猫也,性似猫,此鼠于是乎可用矣,用以捕鼠,群鼠以为鼠也,宁知其柔而害物,同类相残也哉”。也就是说,其他的老鼠还以为它是鼠,比较少地防备它,所以这只大老鼠能够把周边的同类全部消灭掉。
主人自从有了此鼠之后,“群鼠避之,各携其子女以逃,永夜安眠,无窥屋翻盆之苦,无穿墉耗米之忧,鼠诚主人功臣也哉”。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有趣的结尾:久而久之,鼠与主人便像宠物猫与人一样亲密,“行坐追随,近狸奴”。一日,鼠卧于主人之旁,有访客来,见如此硕大的老鼠,大惊,“捶而杀之”。主人十分伤感,“葬之隐处,聚土为邱,亦帷盖之义也”。李调元总结道,这是“以小人攻小人之术也”。开始,要让他们自己互相残杀,“不相杀,无以拔其尤”,就是说最好的选不出来;然后让这些优选的互相撕咬吞噬,“不相食,无以除其害”。其实,从其信中最后一句话,可以看出实际上他是讥讽所谓“以贼治贼”的做法:“以鼠捕鼠,终不若以猫捕鼠为正也。然则以贼治贼,又何如以官治贼哉?居官者当以猫鼠同眠可鉴也。”也就是说官方不能和贼混在一起,如同猫鼠同眠,是十分荒唐的。[17]
那么为什么李调元三次上书严知州,谈控制啯噜的问题?赖安海的《李调元“万卷楼焚”考述》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背景。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李调元家的万卷楼落成,他家的“醒园”紧临夏家湾、廖家沟,是啯噜活动频繁的地方,在第一书中所提到的南村、河村两坝也有以江万明、江万志兄弟为头目的啯噜横行。这时的李调元已经归乡绵州两年多了,过去坚持不与地方官交往,这时也不得不向绵州知州严作明上书,阐明解决啯噜问题的策略。严作明派军打死江万明、江万志后,对李调元所提出的其他建议并不采纳。后因啯噜陈单枪白天窜入醒园行劫,李调元命家丁将其擒获送官,于是写了第二书。在第二书中,他指出啯噜廖老四藏在宋士义家,这个宋士义便是后来焚烧万卷楼的元凶之一。
四川早年因平定金川叛乱(1766—1776),各县设军需局,按田派夫马,以供军用。金川平定后,朝廷明令停收,李调元也拒交战争的加派税赋。严作明见李调元有事相求,亲往醒园催李调元完税,并威胁如果拒交,将依法惩处。但是李调元不予理会,又递《与严署州论啯噜第三书》,以小说“以鼠捕鼠”来讽刺“以贼治贼”的荒谬。就这样,李调元与严作明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严作明暗中令窝藏啯噜廖老四的里长宋士义兄弟,盗去李调元所骑的骡子及衣被。李调元命长子至成都报告四川总督李世杰,按察司将宋氏兄弟抓至省城,年末严作明被革职。这一年是李调元归乡后最为困难的一年,与啯噜结仇,与地方官结怨。
乾隆五十五年,陆鼎任知州。上任不久,即催李调元完税,适遇四川总督孙补山调任两江总督,孙为李调元会试同年。六月孙补山过绵州,知州陆鼎派李调元当里长催夫马钱,遭李调元拒绝,陆乃拘其长孙作为报复,李调元遂亲自当差。孙补山见故人李调元躬立于驿道旁,当即下轿问候。李调元据实相告。孙补山闻说大怒,训斥陆鼎:“李调元身为大员,又现有职(乾隆将他革职之后,又复其官,归乡后食俸绵州),尚充编氓,令当里长出差钱当夫乎?予将来不做总督回家,其亦不免乎?”显然,陆鼎违背了朝廷对有功名士绅和退休官员不服劳役的惯例,孙补山对此非常愤怒,责令陆鼎为李调元除去徭役,陆鼎当天用自己的轿舆,连夜送李调元回家。
嘉庆五年(1800)四月,_攻绵州,建成14年的万卷楼被焚。李调元写道:“蜀中教匪之多,其来有二:一、啯匪处分甚严,官吏率多诲盗,不敢明正典刑,皆暗中处死,贼遂谓官怕啯匪,故反;二、按粮派民,叠加无已,以至民无论贫富皆辛苦,终年不能足食,故从贼反者众,今日之土贼,即将来之教匪,愚所以窃为寒心也。”李调元的这两个说法不一定能充分地解释当时混乱,但是他是身受啯噜之害的退休官员,他这样说一定有相当的道理。这种说法似乎暗示,不少啯噜(“土贼”)参加了_,即所谓“今日之土贼,即将来之教匪”。[18]
李调元还写有《啯噜曲并序》:啯噜本音“国鲁”,“蜀人呼赌钱者,通曰啯噜”。也就是说,在四川,过去称赌博的人为啯噜。他们外出的时候常带刀,短刀叫“线鸡尾”,长刀叫“黄鳝尾”,皆是根据其形状得名。啯噜内部又分为红黑两类,白天活动者称“红钱”,如“剪绺割包”之类,类似于小偷小摸;夜里活动者称“黑钱”,如“穿墙凿壁”之类,类似于强盗。他们“或三五成群,或百千成党”。如果他们人少的时候,则“劫夺孤旅”,就是抢夺单身旅客;人多势众的时候,则胆敢“抗拒官兵”。李调元说他们是四川危害最大的团伙,即“蜀中为害,莫此为甚”,还咬牙切齿地说,“非斩草除根,久必蔓延”。他赞扬一位治理啯噜非常有成效的官员:“公名廷桂,汉军,自公制蜀,此辈敛迹,及去,无不望公再来也。”这里说的“廷桂”,即黄廷桂,他在雍正年间任四川提督。按照李调元的说法,他在四川的时候,由于治理有方,啯噜便销声匿迹了。[19]
有趣的是,李调元还留下了一首《啯噜曲》:“黄鳝长,线鸡短,_兵戈满。黑钱去,红钱来,山桥野店鸡犬哀。杀人不偿命,皆冒古名姓。夜来假面劫乡民,平明县堂充保正。刀为益州剑为阁,天胡不将此辈戮?安得再来关内侯,尽使带牛兼佩犊。”[20]如果我们读了李调元的序,应该对这首曲的基本内容不难理解。黄鳝、线鸡是他们使用的长短武器,在大白天他们也敢抢劫。他们内部也分黑钱和红钱两种,只是行动的时间和方式不同。他们经常在活动的时候假冒姓名,所以来去无踪。甚至他们还胆敢冒充保正,鱼目混珠。益州、剑阁都是四川的地名,四川是他们的活动范围。
总结哥老会的起源 第3篇
对于啯噜的治理,邱仰文说要从社会的最基本做起,首先,“里甲清严”,这样啯噜就没有藏身之地。但是“欲清里甲,非先选保牌不可”。四川流动人口非常多,哪怕是有田产的人,也是来去无定,“尚移此去彼”。目前就是那些“朝东暮西之人”,充当“甲役”,在保甲系统中做事儿的人,难免“有名无实,焉能收效”。所以遴选保正牌头,“必选老干有田业妻室者充之”。选择正确的人去承担地方事务,即“得人任事”,那么就应该是“久住其地”的人。这就要实施门牌的严格监管,“各户门牌,谕令移去者缴除;新增者注册,此为第一要着”。就是说,离开的人就必须从册上去除,而新来的人立刻登记在册。
其次,“必严约束”。就是在执行过程中,必须要严格规则。“事无专责,彼此观望,有事则推诿卸罪”,而有人负责,才可以把事情做好。一旦确定责任人以后,就要“分日稽查,以专责成”。比如说,一个场共有几保,一个保共几牌,共计保牌若干人,每日应某保某牌值日,都要清楚,“发以印簿,行以朱签,俾轮流分査,某值日则签簿俱传,至某保甲家,有无窝匪,一一登注明白,立时举首,自甲而乙,周而复始”。而且一切的巡查,都不要依靠纳税户,即“不累及花名”,“既不繁苛,亦不扰民”。在大的场镇,一人值日显然不够,“耳目难周”,可以分为上、中、下,分界负责,“责任专而约束严矣”。
第三,“必勤巡视”。当官的人要经常到下面去巡查,依靠捕役是不行的,因为他们“职微”,无法“弹压”。如果有实权的官吏,“身任地方,必躬必亲”,特别是那些大场,或者离县城最远,或者与他县界连之处,都是“啯噜最易出没往来”的地方。知县除因事巡查外,每月还应该“减装轻骑,亲临其地”。
第四,要明“赏罚”,因为“空言无补”。如果某场某甲有“窝匪”,那么就必须问责“保牌”“邻右”,而且还要“尽力根究,连坐不贷”。如果发现啯噜,而某场某甲保牌不举报,“别经察出,或花户举首,必立提严处更置”。如果几个月都地方安宁,则要发“慰劳奖藉,极口称道,亲给花红,以激励之,俾无后懈”。
第五,要斩草除根。凡是啯噜有可能逗留的地方,都要抽掉他们的基础。那些荒山孤店,非往来大道,“既无益于行旅,徒有害地方”,要当即“毁其坊巢”。那些开厂的,做生意的,如果接待过啯噜,可以“宽其既往”,但是要令他们“另寻生业,拔尽根株”。啯噜成群结队横行的酒肆、迫协良民的地方,各个县场镇,各户要准备“大棍”一根,上面还要大书“专打拒捕啯噜匪类”八个大字,“立于门首,俾鸣锣为号,齐力擒解”。拿获以后,不得殴打,即“既就拘执,不得攒殴”。这样,哪怕啯噜不是“闻风远遁”,他们“停留犯案,则差稀矣”,也就是会越来越少。
邱的这篇文章写于何时并不清楚,但是肯定在乾隆六年之后,因为他提到“伏查乾隆六年,粤民有给照入川之例,可否比照楚民入川,并行给照”,也就是说乾隆六年的时候,朝廷准许广东的人民按照准许的配额入川开垦,那么湖北是否可以按照这个办法入川呢?来川创业之后,“已成土著,及有亲族依托已久,实为良民,并有资财贸易者,一概不必查究”。但是,楚民入川,“无生理,或单身,或结伴,无论投亲、就业,俱呈明本地该管州县,取具族邻甘结,知照所住地方,注明人数及投托亲族姓名居址,给照准行至川”。也就是说,已经在四川定居下来的移民,已经有了家业,那么就可称为“良民”,不需要查究他们的来历。而新从湖北陆路入川的移民,就要在当地登记,还要签署保证书(“甘结”)。他们所到地方,都要“验照”,相符者,则给予“地牌”,也就是可以开垦的地,“编入烟册”。如果是无照入川,沿途各汛营、州县,要“一体查察,即行递回”。如果有人在四川犯事,“除据情罪,分别问拟”,先查明是否有许可,然后遣送回籍。最后,邱总结了控制啯噜的一整套方案,就是:“清甲清窝,绝其喙息。庶来踪去路,两下查拿,啯噜之名,归于乌有。而教之廉耻,人伦可正;导之任恤,疆理自清,民风渐归淳厚矣。”[11]
邱仰文在《再论啯噜状》中,强调了保甲对肃清啯噜的重要性:“保甲者,治世之纲维也。保甲立,则啯噜清;啯噜清,则保甲肃。”他回忆自己在陕西定远任职时,奉行“保甲九则”:选保牌、严约束、信赏罚、勤巡视、清场镇、察胥役等。对于“土著奸民,外来流棍”,要以“保牌捕役为先务”,要“洞悉民弊”。提出“探其源而治之”的办法,不能扬汤止沸,而是要“灶底抽薪”,才是“省力”的办法。川省“五方杂糅,外来无籍流匪,大都必有土著奸民为之窝”。所谓土著,其实不过是“外来流寓之久者,利其攫掠资财,合伙盘踞,出没为害”。
要清理保甲(“清甲”),就是要“清窝而已”,也就是清理赌窝。所谓“清窝”之法,就是要“悬以赏格”,“确访严拿,净其巢穴”。为官者要“尽力根究”,如果是当地人,就要严加管束;如果是流民,便立即“递还”。而且要一处处清理,即“拿一处则清一处,拿数处则清数处”。啯噜经常聚集在“人烟辐犊、民居比密之区”,窝留者往往也在这些地方。另外,县与县的边界亦是他们的藏匿之所。地方官对于每一县场镇几处,哪里是边界,哪里最易“藏奸”,哪个场客店极多,哪个店尚属清白,等等,都需要清楚和熟悉。
他还指出,按道理说,捕役最清楚“啯噜之情状,路径出入,藏匿寄顿者”,但是为什么“用捕役以治之,又百无一效”?因为啯噜于此县犯案,便逃到彼县,而且他们与捕役“声息相通,因缘为奸”。所以选择捕役,“必择有田业、有妻室人,明白强干老练者”,选充快班和壮班。他最后指出:“总之,清甲为清匪之源,清窝为清甲之根,窝线既清,则保牌戒严、劝惩益为有力。”[12]
当时,官员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办法。乾隆九年,山西监察御史柴潮生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建议,就是要让流民有生计,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凡地方有啯噜害民者,令地方官设法安顿,或给予荒地开垦,或转移执事,各听自变,编入保甲,严加管辖,务使分地散处,勿令其结连一处,则土著流民皆可相安,蜀地亦消隐忧矣。”[13]这个不是简单的只是解决啯噜的问题,而是要解决社会问题。
注:本文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立即后台留言通知我们,情况属实,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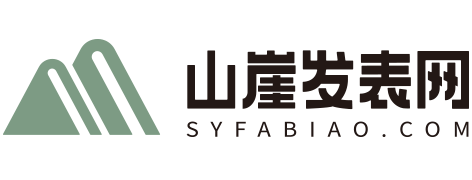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