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汪曾祺
我在七里茶坊住过几天。
我很喜欢七里茶坊这个地名。这地方在张家口东南七里。当初想必是有一些茶坊的。中国的许多计里的地名,大都是行路人给取的。如三里河、二里沟,三十里铺。七里茶坊大概也是这样。远来的行人到了这里,说:“快到了,还有七里,到茶坊里喝一口再走。”送客上路的,到了这里,客人就说:“已经送出七里了,请回吧!”主客到茶坊又喝了一壶茶,说了些话,出门一揖,就此分别了。七里茶坊一定萦系过很多人的感情。不过现在却并无一家茶坊。我去找了找,连遗址也无人知道。“茶坊”是古语,在《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水浒传》里还能见到。现在一般都叫“茶馆”了。可见,这地名的由来已久。
这是一个中国北方的普通的市镇。有一个供销社,货架上空空的,只有几包火柴,一堆柿饼。两只乌金釉的酒坛子擦得很亮,放在旁边的酒提子却是干的。柜台上放着一盆麦麸子做的大酱。有一个理发店,两张椅子,没有理发的,理发员坐着打瞌睡。一个邮局。一个新华书店,只有几套毛选和一些小册子。路口矗着一面黑板,写着鼓动冬季积肥的快板,文后署名“文化馆宣”,说明这里还有个文化馆。快板里写道:“天寒地冻百不咋①,心里装着全天下。”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已经过去,这种豪言壮语已经失去热力。前两天下过一场小雨,雨点在黑板上抽打出一条一条斜道。路很宽,是土路。两旁的住户人家,也都是土墙土顶(这地方风雪大,房顶多是平的)。连路边的树也都带着黄土的颜色。这个长城以外的土色的冬天的市镇,使人产生悲凉的感觉。
除了店铺人家,这里有几家车马大店。我就住在一家车马大店里。

我头一回住这种车马大店。这种店是一看就看出来的,街门都特别宽大,成天敞开着,为的好进出车马。进门是一个很宽大的空院子。院里停着几辆大车,车辕向上,斜立着,像几尊高射炮。靠院墙是一个长长的马槽,几匹马面墙拴在槽头吃料,不停地甩着尾巴。院里照例喂着十多只鸡。因为地上有撒落的黑豆、高粱,草里有稗子,这些母鸡都长得极肥大。有两间房,是住人的。都是大炕。想住单间,可没有。谁又会上车马大店里来住一个单间呢?“碗大炕热”,就成了这类大店招徕顾客的口碑。
我是怎么住到这种大店里来的呢?
我在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下放劳动,已经两年了。有一天生产队长找我,说要派几个人到张家口去掏公共厕所,叫我领着他们去。为什么找到我头上呢?说是以前去了两拨人,都闹了意见回来了。我是个下放干部,在工人中还有一点威信,可以管得住他们,云云。究竟为什么,我一直也不太明白。但是我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我打好行李,挎包是除了洗漱用具,带了一枝大号的3B烟斗,一袋掺了一半榆树叶的烟草,两本四部丛刊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坐上单套马车,就出发了。
我带去的三个人,一个老刘、一个小王,还有一个老乔,连我四个。
我拿了介绍信去找市公共卫生局的一位“负责同志”。他住在一个粪场子里。一进门,就闻到一股奇特的酸味。我交了介绍信,这位同志问我:“你带来的人,咋样?”
“咋样?”
“他们,啊,啊,啊……”
他“啊”了半天,还是找不到合适的词句。这位负责同志大概不大认识字。他的意思我其实很明白,他是问他们政治上可靠不可靠。他怕万一我带来的人会在公共厕所的粪池子里放一颗定时炸弹。虽然他也知道这种可能性极小,但还是问一问好。可是他词不达意,说不出这种报纸语言。最后还是用一句不很切题的老百姓话说:“他们的人性咋样?”
“人性挺好!”
“那好。”
他很放心了,把介绍信夹到一个卷宗里,给我指定了桥东区的几个公厕。事情办完,他送我出“办公室”,顺便带我参观了一下这座粪场。一边堆着好几垛晒好的粪干,平地上还晒着许多薄饼一样的粪片。
“这都是好粪,不掺假。”
“粪还掺假?”
“掺!”
“掺什么?土?”
“哪能掺土!”
“掺什么?”
“酱渣子。”
“酱渣子?”
“酱渣子,味道、颜色跟大粪一个样,也是酸的。”“粪是酸的?”
“发了酵。”
我于是猛吸了一口气,品味着货真价实、毫不掺假的粪干的独特的,不能代替的,余韵悠长的酸味。
据老乔告诉我,这位负责同志原来包掏公私粪便,手下用了很多人,是一个小财主。后来成了卫生局的工作人员,成了“公家人”,管理公厕。他现在经营的两个粪场,还是很来钱。这人紫棠脸,阔嘴岔,方下巴,眼眼很亮,虽然没有文化,但是看起来很精干。他虽不大长于说“字儿话”,但是当初在指挥粪工、洽谈生意时,所用语言一定是很清楚畅达,很有力量的。掏公共厕所,实际上不是掏,而是凿。天这么冷,粪池里的粪都冻得实实的,得用冰镩凿开,破成一二尺见方大小不等的冰块,用铁锹起出来,装在单套车上,运到七里茶坊,堆积在街外的空场上。池底总有些没有冻实的稀粪,就刮出来,倒在事先铺好的干土里,像和泥似的和好。一夜工夫,就冻实了。第二天,运走。隔三四天,所里车得空,就派一辆三套大车把积存的粪冰运回所里。
看车把式装车,真有个看头。那么沉的、滑滑溜溜的冰块,照样装得整整齐齐,严严实实,拿绊绳一煞,纹丝不动。走个百八十里,不兴掉下一块。这才真叫“把式”!

“叭——”的一鞭,三套大车走了。我心里是高兴的。我们给所里做了一点事了。我不说我思想改造得如何好,对粪便产生了多深的感情,但是我知道这东西很贵。我并没有做多少,只是在地面上挖一点干土,和粪。为了照顾我,不让我下池子凿冰。老乔呢,说好了他是来玩的,只是招招架架,跑跑颠颠。活,主要是老刘和小王干的。老刘是个使冰镩的行家,小王有的是力气。
这活脏一点,倒不累,还挺自由。
我们住在骡马大店的东房,——正房是掌柜的一家人自己住。南北相对,各有一铺能睡七八个人的炕,——挤一点,十个人也睡下了。快到春节了,没有别的客人,我们四个人占据了靠北的一张炕,很宽绰。老乔岁数大,睡炕头。小王火力壮,把门靠边。我和老刘睡当间。我那位置很好,靠近电灯,可以看书。两铺炕中间,是一口锅灶。
天一亮,年轻的掌柜就推门进来,点火添水,为我们做饭,——推莜面窝窝。我们带来一口袋莜面,顿顿饭吃莜面,而且都是推窝窝。——莜面吃完了,三套大车会又给我们捎来的。小王跳到地下帮掌柜的拉风箱,我们仨就拥着被窝坐着,欣赏他的推窝窝手艺。——这么冷的天,一大清早就让他从内掌柜的热被窝里爬出来为我们做饭,我心里实在有些歉然。不大一会,莜面蒸上了,屋里弥漫着白蒙蒙的蒸汽,很暖和,叫人懒洋洋的。可是热腾腾的窝窝已经端到炕上了。刚出屉的莜面,真香!用蒸莜面的水,洗洗脸,我们就蘸着麦麸子做的大酱吃起来,没有油,没有醋,尤其是没有辣椒!可是你得相信我说的是真话:我一辈子很少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那是什么时候呀?——一九六○年!
我们出工比较晚。天太冷。而且得让过人家上厕所的高潮。八点多了,才赶着单套车到市里去。中午不回来。有时由我掏钱请客,去买一包“高价点心”,找个背风的角落,蹲下来,各人抓了几块嚼一气。老乔、我、小王拿一副老掉了牙的扑克牌接龙、蹩七。老刘在呼呼的风声里居然能把脑袋缩在老羊皮袄里睡一觉,还挺香!下午接着干。四点钟装车,五点多就回到七里茶坊了。
一进门,掌柜的已经拉动风箱,往灶火里添着块煤,为我们做晚饭了。
吃了晚饭,各人干各人的事。老乔看他的《啼笑姻缘》。他这本《啼笑姻缘》是个古本了,封面封底都没有了,书角都打了卷,当中还有不少缺页。可是他还是戴着老花镜津津有味地看,而且老看不完。小王写信,或是躺着想心事。老刘盘着腿一声不响地坐着。他这样一声不响地坐着,能够坐半天。在所里我就见过他到生产队请一天假,哪儿也不去,什么也不干,就是坐着。我发现不止一个人有这个习惯。一年到头的劳累,坐一天是很大的享受,也是他们迫切的需要。人,有时需要休息。他们不叫休息,就叫“坐一天”。他们去请假的理由,也是“我要坐一天。”中国的农民,对于生活的要求真是太小了。我,就靠在被窝上读杜诗,杜诗读完,就压在枕头底下。这铺炕,炕沿的缝隙跑烟,把我的《杜工部诗》的一册的封面薰成了褐黄色,留下一个难忘的,美好的纪念。
有时,就有一句没一句,东拉西扯地瞎聊天。吃着柿饼子,喝着蒸锅水,抽着掺了榆树叶子的烟。这烟是农民用包袱包着私卖的,颜色是灰绿的,劲头很不足,抽烟的人叫它“半口烟”。榆树叶子点着了,发出一种焦糊的,然而分明地辨得出是榆树的气味。这种气味使我多少年后还难于忘却。
小王和老刘都是“合同工”,是所里和公社订了合同,招来的。他们都是柴沟堡的人。
老刘是个老长工,老光棍。他在张家口专区几个县都打过长工,年轻时年年到坝上割莜麦。因为打了多年长工,庄稼活他样样精通。他有过老婆,跑了,因为他养不活她。从此他就不再找女人,对女人很有成见,认为女人是个累赘。他就这样背着一卷行李,——一块毡子,一床“盖窝”(即被),一个方顶的枕头,到处漂流。看他捆行李的利索劲儿和背行李的姿势,就知道是一个常年出门在外的老长工。他真也是自由自在,也不置什么衣服,有两个钱全喝了。他不大爱说话,但有时也能说一气,在他高兴的时候,或者不高兴的时候。这两年他常发牢骚,原因之一,是喝不到酒。他老是说:“这是咋搞的?咋搞的?”——“过去,七里茶坊,啥都有:驴肉、猪头肉、炖牛蹄子、茶鸡蛋……,卖一黑夜。酒!现在!咋搞的!咋搞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做梦娶媳妇,净慕好事!多会儿?”①他年轻时曾给八路军送过信,带过路。“俺们那阵,有什么好吃的,都给八路军留着!早知这样,哼!……”他说的话常常出了圈,老乔就喝住他:“你瞎说点啥!没喝酒,你就醉了!你是想‘进去’住几天是怎么的?嘴上没个把门的,亏你活了这么大!”
小王也有些不平之气。他是念过高小的。他给自己编了一口顺口溜:“高小毕业生,白费六年工。想去当教员,学生管我叫老兄。想去当会计,珠算又不通!”他现在一个月挣二十九块六毛四,要交社里一部分,刨去吃饭,所剩无几。他才二十五岁,对老刘那样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并不羡慕。
老乔,所里多数人称之为乔师傅。这是个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老于世故的工人。他是怀来人。年轻时在天津学修理汽车。抗日战争时跑到大后方,在资源委员会的运输队当了司机,跑仰光、腊戌。抗战胜利后,他回张家口来开车,经常跑坝上各县。后来岁数大了,五十多了,血压高,不想再跑长途,他和农科所的所长是亲戚,所里新调来一辆拖拉机,他就来开拖拉机,顺便修修农业机械。他工资高,没负担。农科所附近一个小镇上有一家饭馆,他是常客。什么贵菜、新鲜菜,饭馆都给他留着。他血压高,还是爱喝酒。饭馆外面有一棵大槐树,夏天一地浓荫。他到休息日,喝了酒,就睡在树荫里。树荫在东,他睡在东面;树荫在西,他睡在西面,围着大树睡一圈!这是前二年的事了。现在,他也很少喝了。因为那个饭馆的酒提潮湿的时候很少了。他在昆明住过,我也在昆明呆过七八年,因此他老愿意找我聊天,抽着榆叶烟在一起怀旧。他是个技工,掏粪不是他的事,但是他自愿报了名。冬天,没什么事,他要来玩两天。来就来吧。
这天,我们收工特别早,下了大雪,好大的雪啊!
(未完待续)
来源:《收获》1981年第5期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为您推荐↓↓
王雁翔:雪山上的灯光
美文 | 迷失在丽江的街巷
王雁翔:那些孤独的报刊亭
散文丨莫言:吃的耻辱
王朔:回忆梁左
杨绛:《傲慢与偏见》有什么好?
冯骥才: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柴静:有些人的灵魂,能让你记得一辈子
散文丨余秋雨:教师的黑夜
注:本文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立即后台留言通知我们,情况属实,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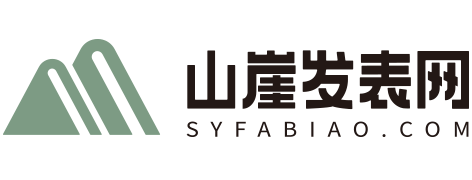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