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词说说心情短语,其意义不仅在于古典诗歌形式的发展与成熟古诗词说说心情短语,更在于诗歌精神的拓进:将中国诗歌精神的深度推向了最本质处,即对人的生存与生活之关注与思考,体现了中国文学对人及其命运的拷问与探索。在《古诗十九首》中,读者能够感受到一般感伤哀怨诗所没有的诗歌精神与悲悯情怀。
01
诗歌与人
人们读诗感受到的诗意是什么?清风明月的闲逸,梧桐细雨的哀怨,金戈铁马的豪情,浅吟低唱的愉悦,这些都是中国古典抒情诗常见的情境古诗词说说心情短语;另一方面,我们往往会从诗歌的时代性与历史意义去肯定一首诗的价值。但伟大的诗歌更是一项关乎自我生活又黏合人类命运的艺术。
诗歌与人之存在的关系,很容易使人想到“人,诗意地栖居”这个命题。这本是海德格尔在阐释荷尔德林诗的时候提出的哲学话题。“‘人,诗意地栖居’这个短语其实是说:诗最先使栖居成为栖居。诗是那种真正使我们栖居的东西。”( [德]海德格尔:《系于孤独之途:海德格尔诗意归家集》,成穷、余虹、作虹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第265页。)这种“诗意”并非美好而虚幻的彼岸花,而是基于劳累的生活,表现人在此岸的存在本质。荷尔德林的诗曰:“如果生活纯属劳累,/人还能举目仰望说:/我也甘于存在吗?是的古诗词说说心情短语!/只要善良,这种纯真,尚与人心同在,/人就不无欣喜/以神性来度量自身。/神莫测而不可知吗?/神如苍天昭然显明吗?/我宁愿信奉后者。/神本是人的尺度。/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我要说/星光璀璨的夜之阴影/也难与人的纯洁相匹敌。/人是神性的形象。/大地上有没有尺度?/绝对没有。”(转引自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德]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10月第1版,第203页)诗中的关键词是“诗意地栖居”“劳绩”“大地”“神性”。“诗意地栖居”是人的本质存在方式;“劳绩”(按:成穷、余虹、作虹译本作“建功立业”)是栖居的具体形态;“大地”是存在的现实基础(人栖居在此岸,非彼岸,亦非“第三条岸”或“别处”);“神性”是一种天空的深邃尺度。
这是西方哲学家对诗意与存在的阐释。“人,诗意地栖居”是存在哲学的命题,而其中的悲悯情怀则是文学的、诗歌的。诗歌的意义并不在于功利的教化,不在于成为经国之大业,而在于悲悯。这对于中外诗歌来说都是普适的,是共同的诗歌精神。《古诗十九首》对人的现实存在、生活状态没有任何回避与粉饰。读者在其中能够发现东西方诗意的共鸣——“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只在“神性”这一层相异)
而人总是存在于具体的时代与社会之中,因此,《古诗十九首》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马茂元先生在《古诗十九首初探》中说:“它围绕着一个共同的时代主题,所写的无非是,生活上的牢骚和不平,时代的哀愁与苦闷,并无任何神秘之处。”“在《十九首》里,表现这种羁旅愁怀的不是游子之歌,便是思妇之词,综括起来,有这两种不同题材的分别,但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马茂元编著:《古诗十九首初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第17页,第18页。)马茂元先生是从社会历史意义来阐释《古诗十九首》的现实性和思想性。然而,从更广阔的视野看,诗中的“牢骚和不平”“哀愁与苦闷”与“纯属劳累”的生活、“充满劳绩”的“诗意地栖居”,不也存在着某种相关性吗?因此,这一组诗歌的意义并不局限于一个社会、一段历史,更是对人类存在问题的揭示与关怀。(下文二、三详述。)一切人类存在的问题归结起来总是一个问题,本质的问题反而正是日常的问题,自然也就“无任何神秘之处”。
优秀的诗歌总是直面人类存在的“劳绩”与悲凉本质,并以各自的方式关怀现实。这无关乎往来古今、南北地方、东西文化。
02
人世之悲
东汉直至魏晋,那么长的一个时代,却是混乱、罪恶、恐怖的,正如曹操之所见:“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按:即《蒿里行》),《曹操集》,中华书局1974年12月第1版,第6页。)
然而,人在本质上还是诗意的,或者是趋向诗意栖居的。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是“充满劳绩”的。“诗意”与“劳绩”同在而又同质。《古诗十九首》揭示人的栖居状态,正是让人们首先睁眼直面人世间无法回避的困境、痛苦、悲观、绝望等一系列的矛盾。
1.死亡——人之存在的最根本困境在混乱的时代,人的生命无法得到保障,死亡是《古诗十九首》悲感的深源。但死亡又岂是战争罪恶时代之特有?这本是人类存在就要面对的问题。人一旦进入存在(所谓“人生”),便进入生与死的矛盾,在不断流逝的时间中,行于成住坏空的过程。无法停留,无法回头,不由自主。可是人渴望永恒“!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生年不满百》)愿之不得而生忧,所以在现实人世中感到悲观。这一根本矛盾导致了变“主”为“客”的心理——对存在的怀疑“: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于是,栖居只是“寄”而已“: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人生在世的主体归属感与存在感消解,代之以寄生之感,可不悲哉?“客”与“寄”传递着深沉而悲凉的诗意。
面对这个矛盾现实,人多么无可奈何。只有逝者如斯的叹息:“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回车驾言迈》)“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东城高且长》)面对生不觉其乐,想到死更不觉超然:“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去者日以疏》)悲凉之余仍是悲凉!
时间之速,人生几何,本是日常之叹。由于更进一步往往是悲凉,大多数人在感叹之余还是回避了事,难得糊涂。回避是一种消极,直面得到的是悲观。能够直面,人生其实就已获得了最大的勇气。深味本质的悲哀需要勇气。
2.孤独——人之存在的又一本质问题 相聚固然使人欢乐:“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今日良宴会》)但是,《古诗十九首》的时代,因为宦游前途不可知、交通阻隔等客观因素,人世间的常态是离散,不是团聚。“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行行重行行》)“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青青河畔草》)“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涉江采芙蓉》)挥之不去的孤独与离愁,是诗歌要让人直面的又一个悲观现实。
孤独并不以空间为限:“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迢迢牵牛星》)孤独不仅是客观存在的处境,更是心灵的寂寞无人知:“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西北有高楼》)孤独不是某一时代、某一社会、某一群体的专利。人性大多喜聚不喜散,可为什么“散”总是常态?即使交通、通信的问题解决了,为什么也没能解决心灵的孤独与离索?一个人又能向谁倾吐自己内心的悲苦?因为人在本质上即是孤独的。梭罗说:“太阳是寂寞的……上帝是孤独的——可是魔鬼就绝不孤独。”“我已经发现了,两条腿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能使两颗心灵更形接近。”([美]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126页,第123页。)诸如契诃夫笔下车夫姚纳的心灵悲苦,在现代仍然是一个存在的困境。
3.世态——更悲凉的社会处境 “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驱车上东门》)人在面对根本存在问题时是平等的。因此,人生虽令人悲,却并不使人恨。
人本应该相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友情的需要,也是人的天性之一。但是在社会之中,不念友谊交情,只因一些俗世的尘埃遮蔽了纯净的心灵,比如功名、富贵、仇恨之类。恨,其实是由人自己培养出来的,因为人世间出现了许多不平等。这些人为的世俗问题,如果也和本质的存在问题一样难以改变,愤激就在所难免:“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青青陵上柏》)“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明月皎夜光》)
信仰上帝的语境也有类似之恨,由此产生罪与罚。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故事。在上帝眼中人本来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人却人为地将人划分为两类——“平凡的人”和“不平凡的人”,“不平凡的人”制定规则,而“平凡的人”只能遵守规则,任人宰割。人都想要自由,趋利避害,所以拉斯柯尔尼科夫不愿像马尔美拉陀夫那样任人宰割,他打算证明自己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人”,走上了“罪”的道路,最终接受了神性的救赎。
人自己造出的罪恶,靠什么来救赎?《古诗十九首》中的抒情者面对这一层问题产生了人生的虚无,抱以激愤的心理,或是游戏人生的心理。
4.虚无——无法返乡的悲凉 《古诗十九首》里弥漫着人生如过客的慨叹,由此对世界产生了一种浓郁的虚无感。游子羁旅行役,功名未就,无法还乡。功名富贵自是虚无,更悲凉的是感到了家园的沧桑与虚无:“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去者日以疏》)返乡因此而无法实现。带着这种悲凉感,诗歌即使在描写美好的事物,如“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青青河畔草》),也令人心生一种悲剧感,不禁会联想到美好事物的流逝与凋零。
想快乐,想相聚,想永恒,可都没有办法。“无”成了永恒。天道本“无”,一切苦与恨,是人间自有或自生的。那么,意义就需要人类自己来赋予。所以,《古诗十九首》揭示了人世之“悲”,也需有基于现实的关怀。
03
生命之悯
荷尔德林在诗中说道,“以神性来度量自身”“神本是人的尺度”“人是神性的形象”。有神性在召唤,其悲悯是基于大地栖居而向上引领的。而中国古诗的关怀还是回到了现实。
1.只在“及时”虽然对“仙人王子乔”的神仙世界有着无限的羡慕与向往,但还是认识到“难可与等期”(《生年不满百》),于是转向现世:“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驱车上东门》)饮酒、被服,这类行乐之举,在看透了存在之悲境后,只可谓一种无奈的现实关怀。更重要的是“及时”的意识:“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冉冉孤生竹》)“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生年不满百》)时间无法停留,也无法逆流,但是却可以珍惜。与时间同行,便能在流驶中找到现实的意义。
及时立德、立功、立言,“倜傥非常之人”如是。但《古诗十九首》表现的是一群中下层文人失意情绪的作品,反映的是大多数平凡人的问题,关怀的出发点也基于人类最基本的意义。诗中某些所谓及时为乐的做法,虽未免为圣贤所轻,却揭示了人类的困境,展现出人类最真诚的心灵,这些诗篇至今仍旧感人至深。
在没有神性尺度的语境中,对于平凡的人来说,他们生活在充满劳绩的大地上,过着劳累的生活,又何尝不是诗意地栖居?建安时代的诗人悲慨于“人生几何”,在现世往往追求建功立业。劳绩与建功立业,二者在现实关怀这个层面并无本质区别。恰如上文所提到的,荷尔德林诗中的“劳绩”一词又被译作“建功立业”。
君不见,一世之雄今安在?君不见,惟有饮者留其名。只是,一切贵在“及时”。
2.虚名有重名《古诗十九首》里有这样一对自相矛盾的诗句:
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明月皎夜光》)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
一个说:因为没有永恒,要那些虚名作什么?
一个说:因为人生短暂,把荣名当作宝贝吧。
一句是悲,一句是悯。平凡而真诚的想法。不能说追求名利就多么可鄙,因为其实他在很艰难地挣扎、劳绩。尚有这一点“荣名”来感动悲哀的心灵,谁能说这样的内心也是污浊不堪的?这大概就是诗意栖居,但又充满劳绩。像谪仙李白一面欲“散发弄扁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一面又念念不忘“愿为辅弼”,谪居人间之仙,也不可避免地要存在于劳绩中。又如柳永虽“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可他羁旅行役,也还是在意过功名的。有人心与神性之存在,“劳绩”并不妨碍“诗意”,“虚名”或是“重名”,并没有本质不同。
许多悲苦只因人不相知,只因无人倾诉。所以,《古诗十九首》中的抒情者最渴望并努力寻求的关怀应该是人之相知,希望得到知音心灵的相互理解与共鸣:“愿为双鸣鹤,奋翅起高飞!”(《西北有高楼》)“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客从远方来》)有此同心,何惧别离。
虽说人世间人心本难测,可也恰是这最难测的心灵,寄托着最美好而永恒的东西。这是平凡之人能够得到的关怀。海德格尔说:“他们就以歌者的忧心倾心于那有所隐匿的切近之神秘了。基于这种统一的对同一者的倾心,忧心忡忡地倾听的人就与道说者的忧心相亲近了,‘他人’就成为诗人的‘亲人’。”([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2月第1版,第32页。)《古诗十九首》并无神秘性,但忧心倾心于共同的人世悲悯,抒情者不亲近吗?读者不倾心吗?
《古诗十九首》佚名的作者们深味于现实人世之悲凉,还能善良地道一句“努力加餐饭”(《行行重行行》),可谓悲凉之余还存有亲人般的真诚关怀与安慰。这一组诗反映的社会或有别于现代,语境或有别于西方,然而其中表现的悲悯情怀是所有诗歌的共同精神,是现代的,也是世界的。
《古诗十九首》之动人不在于亭台楼阁之宏伟绮丽,不在于春花秋月之浅吟悲怀。读之,感受到的是一种大地上的诗意与悲悯,体会到的是人之为人的存在感的共鸣。其艺术魅力正如荷尔德林所说:“如果生活纯属劳累,/人还能举目仰望说:/我也甘于存在吗?是的!”(转引自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德]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10月第1版,第203页。)
>原题《悲悯:〈古诗十九首〉诗意的现代解读》,载《名作欣赏》 2015年第3期
如需参与古籍相关交流,请回复【善本古籍】公众号消息:群聊
欢迎加入善本古籍学习交流圈
注:本文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立即后台留言通知我们,情况属实,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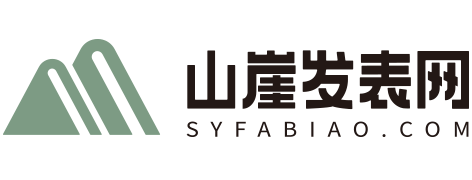
发表评论